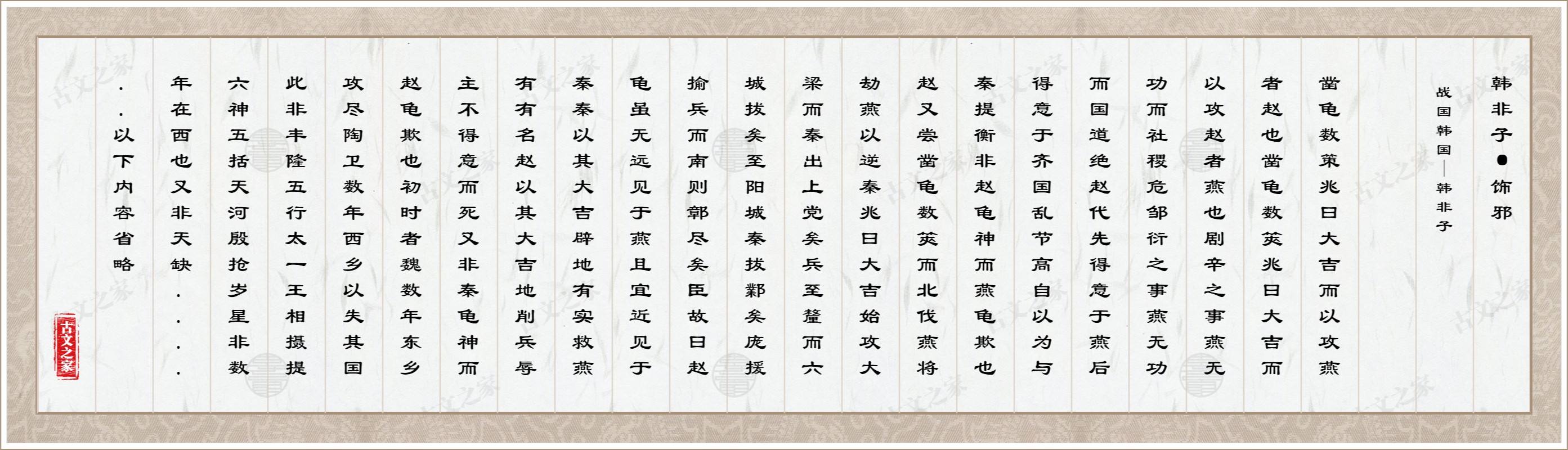- 对照翻译:
凿龟数策,兆曰大吉,而以攻燕者,赵也。
钻烧龟甲、计算蓍草进行占卜,兆象显示“大吉”,因此攻打燕国的是赵国。
凿龟数筴,兆曰大吉,而以攻赵者,燕也。
钻烧龟甲、计算蓍草进行占卜,兆象显示“大吉”,因此攻打赵国的是燕国。
剧辛之事燕,无功而社稷危;
剧辛为燕国效力,没有功劳,却让国家陷入危险;
邹衍之事燕,无功而国道绝。
邹衍为燕国效力,同样没有功劳,却导致国家命脉断绝。
赵代先得意于燕,后得意于齐,国乱节高。
赵国先战胜了燕国,后又战胜了齐国,国内混乱却依然趾高气扬,自以为能与秦国势均力敌。
自以为与秦提衡,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。
这并不是因为赵国的占卜灵验而燕国的占卜骗人。
赵又尝凿龟数筴而北伐燕,将劫燕以逆秦,兆曰大吉。
赵国还曾通过占卜向北讨伐燕国,打算挟持燕国来抗拒秦国,兆象显示“大吉”。
始攻大梁而秦出上党矣,兵至釐而六城拔矣;
刚开始进攻燕国的大梁时,秦国就从上党出兵了,赵军进至厘地时,自己的六个城池已被秦国攻占;
至阳城,秦拔鄴矣;
赵军到达阳城时,秦军已占领了赵国的邺地;
庞援揄兵而南,则鄣尽矣。
等到庞援引兵南下救援时,鄣一带全被秦军占领了。
臣故曰:
所以我说:
赵龟虽无远见于燕,且宜近见于秦。
赵国的占卜即使对攻打燕国缺乏远见,也应对秦攻赵有所预见。
秦以其大吉,辟地有实,救燕有有名。
秦国依据自己的“大吉”兆象,开辟疆土既得实惠,救援燕国又得了美名;
赵以其大吉,地削兵辱,主不得意而死。
赵国依据自己的“大吉”兆象,领土削减、士兵受辱,赵王未能如愿以偿而死。
又非秦龟神而赵龟欺也。
这也并不是因为秦国的占卜灵验而赵国的占卜骗人。
初时者,魏数年东乡攻尽陶、卫,数年西乡以失其国,此非丰隆、五行、太一、王相、摄提、六神、五括、天河、殷抢、岁星非数年在西也,又非天缺、弧逆、刑星、荧惑、奎台非数年在东也。
起初,魏国几年间向东攻下了陶、卫,又有几年向西攻秦却丧失了许多土地,这不是因为丰隆、五行、太一、王相、摄提、六神、五括、天河、殷抢、岁星等吉星有几年都处在西方,也不是因为天缺、弧逆、刑星、荧惑、奎台等凶星有几年都处在东方。
故曰:
所以说:
龟筴鬼神不足举胜,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。
卜筮鬼神不足以推断战争胜负,星体的方位变化不足以决定战争结果。
然而恃之,愚莫大焉。
明明如此,却还要依仗它们,没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。
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,加事于明法。
古代的先王致力于亲近百姓,从事于彰明法度。
彼法明,则忠臣劝;
法度彰明了,忠臣就受到鼓励;
罚必,则邪臣止。
刑罚坚决了,奸臣就停止作恶。
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,秦是也;
忠臣受到鼓励,奸臣停止作恶,因而国土拓展、君主尊贵的,秦国正是这样;
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,山东是也。
群臣结党拉派背离正道营私舞弊,因而国土丧失、君主卑下的,山东六国正是这样。
乱弱者亡,人之性也;
混乱弱小的衰亡,这是人事的一般规则;
治强者王,古之道也。
安定强盛的称王天下,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。
越王勾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,身臣入宦于吴;
越王勾践依仗贵重的龟甲显示的吉兆同吴国打仗,结果失败,自己成了俘虏去吴国服贱役;
反国弃龟,明法亲民以报吴,则夫差为擒。
返国后抛弃龟甲,彰明法度、亲近百姓以求报复吴国,结果吴王夫差被擒获了。
故恃鬼神者慢于法,恃诸侯者危其国。
所以依仗鬼神保佑的就会忽视法治,依仗别国援助的就会危害祖国。
曹恃齐而不听宋,齐攻荆而宋灭曹。
曹国依仗齐国而不服从宋国,齐攻楚时宋灭了曹;
邢恃吴而不听齐,越伐吴而齐灭邢。
邢国依仗吴国而不服从齐国,越伐吴时齐灭了邢;
许恃荆而不听魏,荆攻宋而魏灭许。
许国依仗楚国而不服从魏国,楚攻宋时魏灭了许;
郑恃魏而不听韩,魏攻荆而韩灭郑。
郑国依仗魏国而不服从韩国,魏攻楚时韩灭了郑。
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,主慢而听秦、魏,恃齐、荆为用,而小国愈亡。
如今韩国弱小却依仗大国,君主忽视法治而服从秦和魏,依仗齐和楚作为维持手段,结果使本就弱小的韩国越发趋于灭亡。
故恃人不足以广壤,而韩不见也。
所以依仗别人不足以开拓疆土,而韩国却看不见这一点。
荆为攻魏而加兵许、鄢,齐攻任、扈而削魏,不足以存郑,而韩弗知也。
楚国为了攻打魏国而用兵许、郡,齐国攻打任、扈而侵夺魏地,这都不足以保存韩国,而韩国却不清楚。
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国,恃外以灭其社稷者也。
这些都是不彰明法令治理祖国,却依仗外国而导致祖国灭亡的例子。
臣故曰:
所以我说:
明于治之数,则国虽小,富;
懂得治理的办法,那么国家虽小,也可以富有;
赏罚敬信,民虽寡,强。
赏罚谨慎守信,民众虽少,也可以强大。
赏罚无度,国虽大,兵弱者,地非其地,民非其民也。
赏罚没有标准,国家虽然很大,兵力衰弱的,土地不是自己的土地,民众不是自己的民众。
无地无民,尧、舜不能以王,三代不能以强。
没有土地和民众,尧舜也不能称王天下,夏、商、周三代也不能强盛。
人主又以过予,人臣又以徒取。
君主又因此过分地行赏,臣子又白白地得赏。
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,上任之以国。
对那些不顾法律而谈论先王明君功绩的人,君主却把国事委托给他。
臣故曰:
我所以说:
是原古之功,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。
这是指望有古代的功绩,却拿古代的赏赐标准去奖赏现在的空谈家。
主以是过予,而臣以此徒取矣。
君主因此过分地行赏,臣子因此白白地得赏。
主过予,则臣偷幸;
君主过分地行赏,臣下就会苟且和侥幸;
臣徒取,则功不尊。
臣下白白地得赏,功劳就不再尊贵了。
无功者受赏,则财匮而民望;
无功的人受赏,财力就会匮乏,民众就会抱怨;
财匮而民望,则民不尽力矣。
财匮民怨,民众就不会为君主尽力了。
故用赏过者失民,用刑过者民不畏。
所以行赏不当的就会失去民众,用刑不当的民众就不再畏惧。
有赏不足以劝,有刑不足以禁,则国虽大,必危。
有赏赐却不足以勉励立功,有刑罚却不足以禁止邪恶,那么国家即使很大,也一定很危险。
故曰:
所以说:
小知不可使谋事,小忠不可使主法。
有小聪明的人不能让他谋划事情,有小忠诚的人不能让他掌管法令。
荆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,荆师败,恭王伤。
楚恭王和晋厉王在鄢陵交战,楚军失利,恭王受伤。
酣战,而司马子反渴而求饮,其友竖谷阳奉卮酒而进之。
战斗正激烈时,司马官子反口渴要水喝,他的亲信侍仆谷阳捧了一卮酒给他。
子反曰:
子反说:“
去之,此酒也。
拿走,这是酒。”
竖谷阳曰:
侍仆谷阳说:“
非也。
这不是酒。”
子反受而饮之。
子反接过来喝了。
子反为人嗜酒,甘之,不能绝之于口,醉而卧。
子反喜欢喝酒,觉得酒味甘甜,不能停下不喝,结果喝醉后睡着了。
恭王欲复战而谋事,使人召子反,子反辞以心疾。
恭王想重新开战并和他谋划战事,派人叫子反,子反借口心病而加以推辞。
恭王驾而往视之,入幄中,闻酒臭而还,曰:
恭王乘车前去看他,进入帐中,闻到酒气而返回,说:“
今日之战,寡人目亲伤。
今天的战斗,我自个眼睛受了伤。
所恃者司马,司马又如此,是亡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。
我所依赖的是司马,司马又这般模样,这是不顾楚国的神灵,不关心我的民众。
寡人无与复战矣。
我不能和敌人重新开战了。”
罢师而去之,斩子反以为大戮。
于是引兵离开鄢陵,把司马子反处以极刑。
故曰:
所以说:
竖谷阳之进酒也,非以端恶子反也,实心以忠爱之,而适足以杀之而已矣。
侍仆谷阳进酒,并非本来就恨子反,而是真心地忠爱子反,但最终却恰好因此而害了他。
此行小忠而贼大忠者也。
这就是行小忠而害大忠。
故曰:
所以说:
小忠,大忠之贼也。
小忠是对大忠的祸害。
若使小忠主法,则必将赦罪,赦罪以相爱,是与下安矣,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。
如果让行小忠的人掌管法制,那就必然会赦免罪犯加以爱护,这样他同下面的人是相安了,但却妨害了治理民众。
当魏之方明《立辟》、从宪令行之时,有功者必赏,有罪者必诛,强匡天下,威行四邻;
当魏国正在彰明立法、从事法令建设的时候,有功者必赏,有罪者必罚,强盛得可以匡正天下,威势达到四邻诸侯;
及法慢,妄予,而国日削矣。
等到法令懈怠,赏赐混乱,国家就日益衰弱了。
当赵之方明《国律》、从大军之时,人众兵强,辟地齐、燕;
当赵国正在彰明国律、从事军队建设的时候,人多兵强,攻占了齐、燕的土地;
及《国律》满,用者弱,而国日削矣。
等到国律懈怠,执政者软弱,国家就日益衰弱了。
当燕之方明《奉法》、审官断之时,东县齐国,南尽中山之地;
当燕国正在彰明奉法、重视政府决策的时候,东向把齐国作为自己的郡县,南向完全占领了中山的国土;
及《奉法》已亡,官断不用,左右交争,论从其下,则兵弱而地削,国制于邻敌矣。
等到奉法丢弃,政府决策不再实行,左右亲信相互争斗,君主听从臣下决策,于是兵力削弱,土地削减,国家也就受制于邻国了。
故曰:
所以说:
明法者强,慢法者弱。
严明法制的国家就强大,轻忽法制的国家就弱小。
强弱如是其明矣,而世主弗为,国亡宜矣。
强弱对比是如此的分明,而当代君主却不实行,国家危亡真是活该了。
语曰:
俗语说:“
家有常业,虽饥不饿;
家里有固定产业,即使荒年也不会挨饿;
国有常法,虽危不亡。
国家有固定法制,即使危险也不会衰亡。”
夫舍常法而从私意,则臣下饰于智能;
舍弃固定法制而顺从个人意志,臣下就会粉饰自己的智能;
臣下饰于智能,则法禁不立矣。
臣下粉饰自己的智能,法律禁令就站不住脚。
是亡意之道行,治国之道废也。
这样,随心所欲的做法就通行,以法治国的原则就废弃了。
治国之道,去害法者,则不惑于智能,不矫于名誉矣。
治理国家的原则,舍弃危害法令的,就不会受智能的迷惑,不会被虚名所欺骗了。
昔者舜使吏决鸿水,先令有功而舜杀之;
过去舜派官吏排泄洪水,早于命令而抢先立功的,舜把他杀了;
禹朝诸候之君会稽之上,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。
禹在会稽山上接受诸侯国君的朝见,防风氏迟到而禹杀了他。
以此观之,先令者杀,后令者斩,则古者先贵如令矣。
由此看来,先于命令的杀,后于命令的也杀,那么古代首先重视的是依法办事。
故镜执清而无事,美恶从而比焉;
所以镜子保持清亮而不受干扰,美丑就会因此显示出来;
衡执正而无事,轻重从而载焉。
衡器保持平正而不受干扰,轻重就会因此衡量出来。
夫摇镜,则不得为明;
摇动镜子就不能保持明亮。
摇衡,则不得为正,法之谓也。
摇动衡器就不能保持平正,说的就是“法”。
故先王以道为常,以法为本。
所以先王把道作为常规,把法作为根本。
本治者名尊,本乱者名绝。
法制严明,君主名位就尊贵,法制混乱,君主名位就丧失。
凡智能明通,有以则行,无以则止。
凡是智能高强的人,有依据就行动,没有依据就停止。
故智能单道,不可传于人。
所以智能是偏道,不能传给人。
而道法万全,智能多失。
道和法是万全的,智能多有偏失。
夫悬衡而知平,设规而知圆,万全之道也。
悬挂衡器才知道平不平,设置圆规才知道圆不圆,这是万全之道。
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,故佚而有功。
因为明君能使百姓用道来整饬自己,所以省力而有功。
释规而任巧,释法而任智,惑乱之道也。
丢掉规矩而单凭技巧,放弃法治而单凭智慧,是使人迷惑混乱的办法。
乱主使民饰于智,不知道之故,故劳而无功。
昏君使民众用智巧粉饰自己,是不懂道的缘故,所以劳而无功。
释法禁而听请谒群臣卖官于上,取赏于下,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。
放弃法令而听从请托,群臣在上面出卖官爵,从下面取得报酬,所以利益归于私门而权势落于群臣。
故民无尽力事主之心,而务为交于上。
所以百姓没有尽力侍奉君主的心意,而致力于结交大臣。
民好上交,则货财上流,而巧说者用。
百姓喜欢结交大臣,财货就向上流入大臣之手而花言巧语的人就被任用。
若是,则有功者愈少。
假如形成这种局面,有功的人就越来越少。
奸臣愈进而材臣退,则主惑而不知所行,民聚而不知所道。
奸臣越来越得到进用而有才能的臣子遭到斥退,君主就会迷惑而不知道干什么好,百姓聚集起来也不知道往哪儿走。
此废法禁、后功劳、举名誉、听请谒之失也。
这是废法令、轻功劳、重名声、听请托的过失。
凡败法之人,必设诈托物以来亲,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。
凡是败坏法制的人,一定会设下骗局,假托有事来亲近君主,又喜欢谈论天下少见的东西。
此暴君乱主之所以惑也,人臣贤佐之所以侵也。
这就是暴君昏主受迷惑、贤人佐臣受侵害的原因。
故人臣称伊尹、管仲之功,则背法饰智有资;
所以臣子称颂伊尹、管仲的功劳,违法弄智就有了根据;
称比干、子胥之忠而见杀,则疾强谏有辞。
称颂比干、伍子胥的忠贞被杀,急切强谏就有了借口。
夫上称贤明,不称暴乱,不可以取类,若是者禁。
前者称说君主贤明,后者说君主暴乱,不可以拿来类推,像这样的就应禁止。
君子立法以为是也,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为非者,是邪以智,过法立智。
君主立法认为正确的,现在臣子多标榜个人智巧来否定国法,这就是用智巧来肯定奸邪,诋毁法制、标榜智巧。
如是者禁,主之道也。
像这样的应予禁止,这是做君主的原则。
明主之道,必明于公私之分,明法制,去私恩。
做明君的原则,一定要明白公私的区别,彰明法制,舍弃私人恩惠。
夫令必行,禁必止,人主之公义也;
有令必行,有禁必止,是君主的公义;
必行其私,信于朋友,不可为赏劝,不可为罚沮,人臣之私义也。
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私利,在朋友中取得信任,不能用赏赐鼓励,不能用刑罚阻止,是臣子的私义。
私义行则乱,公义行则治,故公私有分。
私义风行国家就会混乱,公义风行国家就会平安,所以公私是有区别的。
人臣有私心,有公义。
臣子有私心,有公义。
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,居官无私,人臣之公义也;
修身廉洁而办事公正,做官无私,是臣子的公义;
污行从欲,安身利家,人臣之私心也。
玷污品行而放纵私欲,安身利家,是臣子的私心。
明主在上,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;
明君在上,臣子就去私心行公义;
乱主在上,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。
昏君在上,臣子就去公义行私心。
故君臣异心,君以计畜臣,臣以计事君,君臣之交,计也。
所以君臣不一条心,君主靠算计蓄养臣子,臣子靠算计侍奉君主,君臣交往的是算计。
害身而利国,臣弗为也;
危害自身而有利国家,臣子是不做的;
害国而利臣,君不为也。
危害国家而有利臣子,君主是不干的。
臣之情,害身无利;
臣子的本心,危害自身就谈不上利益;
君之情,害国无亲。
君主的本心,危害国家就谈不上亲近。
君臣也者,以计合者也。
君臣关系是凭算计结合起来的。
至夫临难必死,尽智竭力,为法为之。
至于臣子遇到危难一定拚死,竭尽才智和力量,是法度造成的。
故先王明赏以劝之,严刑以威之。
所以先王明定赏赐来加以勉励,严定刑罚来加以制服。
赏刑明,则民尽死;
赏罚分明,百姓就能拼死;
民尽死,则兵强主尊。
百姓拼死,兵力就会强盛,君主就会尊贵。
刑赏不察,则民无功而求得,有罪而幸免,则兵弱主卑。
刑赏不分明,百姓就会无功而谋取利益,有罪而侥幸免罚,结果是兵力弱小,君主卑下。
故先王贤佐尽力竭智。
所以先王贤臣都竭力尽心。
故曰:
所以说:
公私不可不明,法禁不可不审,先王知之矣。
公私不可不明,法禁不可不察,先王是懂得这个道理的。